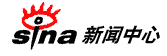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文化新闻 > 新闻报道 |
|
   作者:尹鸿 任何过渡时代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在政治/道德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作为中国主流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 影”,在默默地坚守和生长着。 当我们被《橄榄树下的情人》这样朴素地展示人性善恶的伊朗电影所打动,被《中央车站》这样细腻地揭示人与人之 间的隔膜和沟通的巴西电影所感染,被《美丽人生》这样凄苦地叙述生命故事的意大利电影所征服,被《香港制造》这样富于 想像力地表达都市人困惑和迷乱的香港影片所震动,被《青青校树》、《给我一个爸》这样娓娓地透视人的心灵的捷克电影所 吸引的时候,甚至也被《真实节目》这样深刻地揭示当代人梦幻困境的美国电影所惊异的时候,反省我们的中国电影,也许, 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电影所缺乏的绝不仅仅是电影市场运作机制,金钱和技术,也不仅仅是艺术能力和艺术想象,最缺 乏的是一种对于电影的真诚,对于艺术的真诚,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人的真诚。 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 电影在我们许多的电影人那里,只是获取社会位置和商业利益的一种途径、一个手段,而不是对于人、对于生命、对 于心灵的观照、呵护和热爱。媚权的电影、媚俗的电影充斥我们的银幕;汹涌澎湃的功利主义欲望淹没了相濡以沫的人文关怀 ;急功近利、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使得中国电影正在远离真诚,也在远离人们的心灵。这种无往不在的实用主义精神甚至在中 国最优秀的电影人那里也时隐时现,所以才会出现陈凯歌《荆柯刺秦王》那样赤裸裸的既媚俗也媚雅,既媚中也媚外,既造作 又滑稽的“不伦不类”的伪艺术,才会出现张艺谋明显受到阿巴斯等伊朗导演影响的《一个也不能少》中某些显然迎合势利需 要的设计和构思,尽管这部影片在当今的中国影坛上已经是难得的有诚意和有艺术个性的例外之一。 在如今我们国产电影的银幕上,如果说那些英雄时代的创世回忆,清官良民的盛世故事,善男信女的劝世寓言构成了 所谓主旋律政治/道德电影的主体的话,那么那些喜说戏说的滑稽演义,腥风血雨的暴力奇观则构成了中国商业/娱乐电影的 基础,这两种电影不仅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主流,而且也因为功利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驱动成为了各种传媒播旗呐喊、推波助澜的 主题。然而,无论是以传达主流意识为目的或是以满足大众心理欲望为动机的,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 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甚至无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现实体验。许多影片在粉饰现实的同时也在粉饰人性, 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苦多乐少的生命经历,人不能回避的创伤,都在这些电影中缺席,不少中国电影所虚构的现 实图景和人性世界都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图景和所内省到的人性世界大相径庭。电影在不同程度上割裂了我们与现实人生和 人生体验的血脉联系,电影人也在这些电影交易中泯灭了自己的真诚。电影中没有人的真性情、真体验、真血肉--这正是中 国电影最刻骨铭心的悲哀。 另外一种电影 任何过渡时代其实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应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而且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电影的时期 。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 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 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 需要电影,当然不仅仅是需要电影教导我们如何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也不仅仅只是需要电影带给我们一段短暂的梦幻想象 和心理刺激,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 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悯、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 然而,这一切恰恰被我们绝大多数电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在我看来,与其说,我们本土电影的危机来自好莱坞电影 的冲击,毋宁说更多地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电影脱离了人文关怀,也脱离了我们对于电影的期待。电影中 如果仅仅只是歌功颂德、歌舞升平或者仅仅只是柳暗花明、善恶有报,那么这样的电影只不过是一种供人掩嘴一笑的弄臣小玩 意儿而已,与艺术无关。 但我相信,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我们还可以寻找到“第三种电影”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我 们还可以期待一些真诚的电影的出现。我相信,这样的电影将不再是对好莱坞和花冠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的翘 首以待,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 望人生,与我们对话。 应该说,9O年代以来,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作为主流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依然 还是在默默地坚守和生长着。这些影片虽然一直不是电影市场运作和电影政治活动的中心,但却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最具艺术震 撼力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李少红的《四十不惑》、《红西服》,宁赢的《找乐》、《民警故事》,刘苗苗的《杂嘴子》,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也不能少》,黄亚洲的《没事偷着乐》,黄建新的《站直了别趴下》、《 背靠背脸对脸》、《埋伏》、《红灯停绿灯行》等系列影片,特别是9O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新生代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 巫山云雨》、《城市爱情》、《美丽新世界》、《那人那山那狗》、《天字码头》、《爱情麻辣烫》、《成长》等,都显示了 一种对人性、艺术和电影的真诚。这些影片最基本的艺术动机不是去演绎先验的道德政治寓言或政治道德传奇,也不是去构造 一个超现实的欲望奇观或梦想成真的集体幻觉,而是试图通过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的再现和对离合悲欢的普通平民命运的展 示,不仅表达对转型期现实的体验,而且也表达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渴望、意志、智慧和希冀。 过渡时代的中国体验 于是,从《背靠背脸对脸》中“机关算尽”的王双立屡次争取“正科级”文化馆馆长而不得,到《埋伏》中那位吸毒 者一夜之间摇身成为救人英雄的荒诞,可以看到一种睿智的后现代调侃,是平时人们耳闻目睹的各种道德神话的一个默默的象 喻。而《埋伏》则将“喜剧英雄”的原型做了更为深刻的演绎:两位忠于职责的保卫干部被指派到一个“最不重要”的岗位上 执行监督任务,俩人用最大责任心来完成这一“最无价值”的任务,罪犯终于被抓到而这两位执行监督任务的小人物却被遗忘 和忽略了,但他们仍然夜以继日坚守岗位,俩人中一位因病不治而牺牲,另一位也奄奄一息。最后罪犯供认,他之所以落网并 不是因为那些自认为重要的警察的高明,而是因为那两位被安排到最不重要位置上的监视人的功劳,于是这两人才被记忆,才 偶然间成为了英雄、烈士。于是,渺小和伟大、英雄和小人物、重于泰山与轻如鸿毛之间那种传统的理性联系被解构了,对英 雄、对“人民”、对牺牲、对使命的天经地义的传统解释被这个故事变成了一种荒诞。偶然性冲淡了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 性,人生、特别是小人物的人生更加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这是一种对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家园感觉和人生意义的一种悲天悯 人的质疑,也是对主流文化将人生困境化作“冲突--解决”的戏剧性模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在这些真诚电影中,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根据刘恒小说改编的电影《没事偷着乐》则在当今中国两极分化、 生活方式分化的不平衡背景下,叙述了一些普通平民的生存困境和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没事偷着乐》叙述了当代中国那些 曾经被看作社会脊梁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大民和他的一家,像许多被这个灯红酒绿的时代所遗忘的普通平民一样,在生 活内忧外患的逼迫下,仍然活着,而且用贫嘴、用粗茶淡饭来使自己活得有人的尊严、人的快乐。大民一家生活的那个狭窄、 拥挤、憋闷的家庭空间,既是故事演绎的舞台,也是对这些人在当代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隐喻。从大民一家,我们看到了中 国文化历来所炫耀的一种生命力,无论是多么艰难的生存空间、也无论是面对多么不平衡的利益分配,他和他们都能“像”人 一样活着、笑着、“贫”着--没事偷着乐。而对生存的艰辛,这部影片营造了一种苦涩的幽默风格,用人物的自我作践、自 我安慰、自我解嘲来化解现实矛盾,而观众也在人物的这种苦涩的幽默中产生理解、同情和松弛。一方面是高消费阶层的纸醉 金迷,另一方面则是底层平民的生存挣扎,这不仅是一种物质现实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冲突的揭示。尽管这些影片最 后都通过一种有意识的虚构来为底层平民提供一种进入“幸福生活”的承诺,张艺谋在《一个也不能少》中利用“媒介神话” 解救了面临失学的魏敏芝们,而《没事偷着乐》则用地平线上的一排新楼为几乎无家可栖的大民一家描绘了一幅未来远景,然 而,这些影片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些勉强的抚慰,而是在于它们成为了当前中国现实境遇的一种文化再现。 遭遇美丽新世界 铺天盖地的各种豪华汽车、别墅、化妆品、名牌服装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各种宾馆饭店的灯红酒绿似乎都在承诺“美 丽新世界”就在我们面前,近在咫尺,然而这些幸福生活又几乎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遭遇的是一 个充满诱惑而又无法摆脱匮乏、充满欲望而又充满绝望的世界。于是,我们在由青年导演施润久拍摄的影片《美丽新世界》结 束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段落:在滂沱大雨中,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张宝根拉着金芳的手,站在建筑工地的地基上,指着空中斩钉截 铁地说;这上面有一套属于他宝根猜奖赢得的两居室的房……。这位幸运获得一套迟迟拿不到手的住房的乡下青年宝根来到上 海,为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承诺而留在一个他过去从不认识的远房亲戚年轻的金芳阿姨家。于是,如同所有的普通百姓一 样,他们使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苦苦地生活着,艰难地期望着,而那套两居室的住房则永远作为一个承诺,像一座空 中的楼阁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海市蜃楼。这个用空中楼阁所象征的“美丽新世界”将普通生活的渴望者和劳动者的 生存处境和生存理想深刻而细致地描绘了出来。就像另外一部年轻导演拍摄的影片《网络时代的爱情》中一个大学毕业生所说 :看到到处都是汽车别墅,我就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普通人所梦想的那个美丽新世 界似乎就像宝根所期待的那个空中楼阁。《美丽新世界》的片名就像《没事偷着乐》、未改名为《红西服》以前的《幸福大街 》,以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它们的片名都共同地用幸福、快乐来与人们所遭遇的现实的艰辛形成对比, 暴露了当前失衡状态中消费社会的欲望与匮乏之间的裂缝。 急剧的社会变迁引起人们的心理失衡,是当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体验到的生存现实,而这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流行的一个词汇“下岗”。影片《红西服》所叙述的就是一个经历和面对“下岗”的家庭的故事。但它不 仅仅是一个关于“下岗”、关于下岗工人如何再上岗的劝世故事,而是一个女人如何用自己的坚强和善良来支撑生活和家庭的 故事,一个男人如何在失重和无奈中依靠家的庇护走出困境的故事,一个家庭如何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 故事。下岗只是一个背景,只是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位置颠覆、价值观念颠覆的一个时代性隐喻,这一隐喻在影片中一群已 经失去社会位置的下岗工人含泪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段落中、在中学生明晓发现她心中的偶像变成了平凡人的段落中得 到了充分传达。对于观众来说,下岗也许很远,但转达型却在身边。如同另外一部以“下岗”事件为题材的影片《天字码头》 一样,人们都会不期而然地面对茫然失措、面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荒诞和尴尬,影片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温暖、 一丝抚慰,家成为了抵挡惊涛骇浪的诺亚方舟,关怀成了被社会遗忘和抛弃的边缘人们赖以安慰的一线阳光。 第三种电影的微光 从这些为数不多的面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现实的电影中,我们感受到了种种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这些影片因 为对当下中国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 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观众从那些仿佛生活在周围的“熟悉的陌生人”所经历的事件中,从平日的那些司空 见惯的行为中体会到了其中常常被忽视的生命的哀乐,传达出了一种对于人和生活的关怀。这些作品不仅以其真实而且也以其 人文关怀为观众带来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尽管这一类型的作品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电影文化的主流,但是它们无论是对 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电影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文化发展高度的 一种标志。 尽管好莱坞依赖于其强势力量,正在继续将全世界变成美国电影的超级市场,但是,近年来,欧洲艺术电影的坚守, 日本新电影的崛起,东欧国家优秀电影的不断出现,伊朗电影的独树一帜,韩国电影的本土追求,也都对好莱坞电影帝国提出 了挑战。如果说物质产品的垄断是对消费者的专制的话,那么精神产品的垄断则是对我们文化精神多元需求的剥夺。好莱坞电 影,不是唯一的电影,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东方文化历史和承受着浩大的现实磨难的民族来说,好莱坞电影更不可 能替代我们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因而,我们期待,在我们银幕上那些哭天呼地的煽情故事,刀光剑 影的血腥场面,充满弑父传奇的神秘宅院,遥想当年的创世记忆之外,能够出现更多的“真诚”的电影,我们能够从这些电影 中看到普通人的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境遇,感受到对个体命运的关怀。这样的影片将因为对当下中国人的关怀而显示出其艺术作 为人的艺术所具有的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从而与大众共享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而与观众达成视界的融合。正方兴未 艾的“第三种电影”也许会给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带来一片新的曙光。近一段时期,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霍建起 的《那人那山那狗》等影片在威尼斯、蒙特利尔获奖的消息也许正暗示了“真诚”正在成为一种艺术力量,与亚洲、西欧、东 欧、美洲的所有“真诚电影”一起,形成了一种比好莱坞电影更人性、更关怀、更丰富的世界性的艺术电影思潮,而且正在征 服越来越多的真正热爱电影如同热爱人生一样的人们。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新闻 > 新闻报道 | ||||
网站简介 | 网站导航 | 广告服务 | 中文阅读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帮助信息
Copyright(C) 1999 sina.com, Stone Rich S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